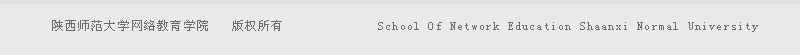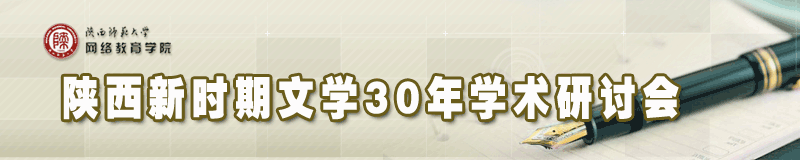
陕西新时期文学30年的辉煌与缺失——与墨共舞,以坚其志,以洁其身
文/图记者张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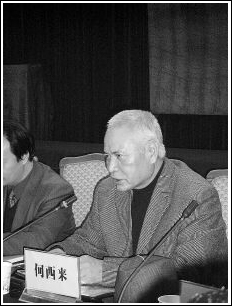
何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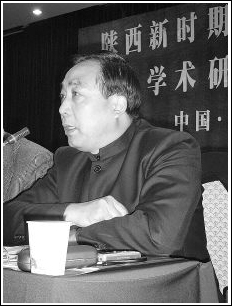
白描
陕西新时期文学30年,走出了三代作家。他们站在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这些先辈作家筑就的基础上,甘于清贫、寂寞,深入生活,直面社会,思考人生,以其深厚的文学底蕴,突出的成就,一次次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创作景观。从上世纪80年代陕西作家群体的形成,到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及至2007年陕西省作协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前后,陕西作家创作再次呈现“井喷”之势,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铸就了陕西文学的辉煌。30年来,陕西文学差不多见证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有时还开了风气之先。然而,有辉煌也有缺失或不足。近日,六十多位作家评论家汇聚一堂,就“陕西新时期文学30年”的话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
地域因素
三大文化板块造就不同创作风格
如果梳理新中国的文学史,陕西文学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什么这片土地孕育了这么多伟大的作品?为什么这些作品又都如此厚重?很多评论家不约而同地把原因之一归结为地域因素。评论家何西来是这样说的:“作家的成功,有其自身条件、时代条件,但因为地域文化的承传,某个地区集中出现一批作家也是必然的。陕西是一个文化传统深厚的地方,区域特色鲜明,陕西的作家被三秦大地哺育,扎根在黄土地上,所以他们不是追新潮追时髦的高手,但会更多地去关注历史、关注人民。”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白描将陕西作家成功的因素归结为五大点,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丰厚的地域文化背景。他认为陕西作家都有一块自己坚守的领地,比如三个领军人物陈忠实、路遥和贾平凹。其中陈忠实代表了平原精神气质形态,坚密厚实;路遥代表了高原精神气质形态,开阔豁达;而贾平凹代表了山地精神气质形态,灵秀俊逸。白描说:“陕西三个地理版块,三个文化版块,造就了陕西作家的写作风格,这风格是和故乡的地理人文环境相通的,是和故乡的山水土地赋予他们的性格相一致的。”白描的这种观点也得到了青年评论家李建军的认可,他认为陕西作家的精神气质高原型雄浑、沉重、淳朴,平原型中正、沉稳、舒缓,而山地型轻扬、灵脱、善变。
陕师大教授李震在把陕西的文化传统按地域因素归结为陕南、陕北、关中三种文化的同时,认为除了这三种文化外,陕西还有一种胡夷文化不容忽视,其代表作家作品包括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叶广芩的家族系列小说,以及红柯的作品等,不能归结为陕西传统的三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但是有其自身之特点,值得研究。
乡土情结
陕西作家的血脉之源
有人说,新时期陕西作家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是支精英队伍却很少有人接受过精英教育,反而在该接受教育的时候饱经磨难。也有人说,陕西的知名作家除个别人生长在城市外,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对土地和农民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和血脉之情。也许正因为来自乡村,饱经磨难,所以从整体上观照,陕西作家以书写“乡土”文学著称于文坛,他们对土地和农民的关注源于他们的地缘情结——乡土情结。白描说:“在生活的底层品尝人生的况味,在苦难中体察普通劳动大众的思想感情,这似乎成为陕西作家的一种天然禀赋,也构成了他们特有的生活资源和情感资源优势。”宝鸡文理学院教授赵德利也说:“乡土情结是陕西作家创作的素材来源,又是他们创作的动力与价值坐标。”何西来认为陕西作家身上的乡土情结是与生俱来的,即使在城市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也不会随着距离的扩大而缩小或消失。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杨琳指出,近年来对乡土无法割舍的情结是西部作家创作的母题之一,他们对故乡由赞美到反思,到不知所措,作品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缺失流露出了深深的眷恋。
与会专家同时也指出,对于土地的依恋,既促成陕西作家推出了一部部厚重的作品,也使陕西作家的思想观念与审美境界受到它的很大影响,他们创作中的缺失和不足也正是源于此。白描很尖锐地指出:“当一个作家用农民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来对历史进程作出估价,来看待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并作出评判的时候,就有点不可靠了。”
文学传统
继承与突破的嬗变
陕西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学传统,这强大的文学传统的熏陶,文学前辈对文学新人成长提供的环境和氛围,都成为陕西文学人才脱颖而出的有效的孵化器。白描说陕西的文学传统包括从柳青等作家就开始的作家要深入生活的传统,也包括做人实在,写作也实实在在的文学创作态度,还包括陕西作家在生活的磨砺中体味人生,从而保持贫民意识和民间文化创作视角等。这些都是现当代作家必须坚持和守望的优秀的传统。
陕师大教授张国俊从文学创作本身的角度出发,指出柳青开启了一种文学传统,陕西文学的成功与柳青带出来的一代中青年作家是分不开的,陕西作家大多数都是从崇拜柳青、学习模仿柳青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们从柳青身上学到了文学的执著,也学到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甚至连柳青的语言都对他们影响很大,从而形成了学界所说的“柳青体”。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陕西新时期文学的前期成就可以归结为继承柳青的结果,后期之成就则是超越这种影响的结果。陕西文学的优秀传统应该得以继承,但是从文学创作本身而言,当代作家必须有所超越,有所突破。
发展隐忧
“70后”作家的集体缺失
研讨会上,作家评论家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的文学成就,同时也直面陕西文学发展的隐忧。这隐忧主要来自陕西“70后”作家的集体缺失。新时期以来陕西有三代作家:第一代是包括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在文坛已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家;第二代是以红柯、杨争光、叶广芩等为代表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作家;第三代是七零年后出生的作家。李震指出:“在上世纪末,‘70后’作家集体登场之际,我们很悲哀地发现,其中少了陕西作家的身影。”而李建军也忧虑地指出,陕西三代作家中,第一代作家和第二代作家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隔绝,结果是第一代作家遮蔽了第二代作家,而他对陕西第三代作家几乎没有任何印象。赵德利则针对当下陕西文学无力“东征”的疲软现象分析说,由于年龄等因素,第一代作家的创作力大多已经衰退,第二代作家虽然年富力强,但是地域个性缺损,而第三代创作力的匮乏,更令人心痛。
对“70后”作家的集体缺失,专家们分析说,一方面,陕西作家深处内陆,没有广州、上海等开放城市生活的经验,所以必然没有卫慧、棉棉等新生代作家的生命体验,无法写出新新人类的城市生活小说;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陈忠实等老一辈作家的生活磨砺和生存体验,无论是文化积淀还是生活积累,都让他们无法推出像《白鹿原》式的厚重作品,所以这是陕西文学发展的隐忧,也是必然要经过的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