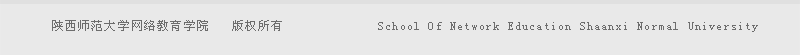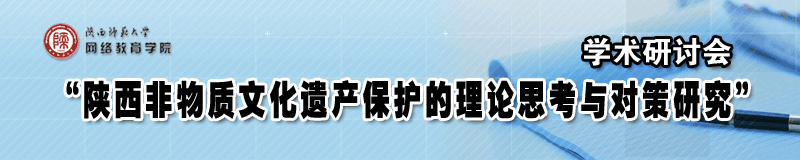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走出新旧对立的误区
――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论文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三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我国政府和广大群众高度关注,我国不仅有四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目前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国家还先后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确定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即遗产持有者。随着“原生态歌曲”大奖赛等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社会流行的词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展览、表演,也在国内国外如火如荼进行,如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和最近成功举办的北京奥运会等重要活动,也有我国非物质遗产的表演展现,吸引了世界各国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几乎是突然降临,但已悄然引发一系列文化价值观的重大变革。如何对待传统,如何评价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如何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思想的活跃与解放,同时也凸显出过去长期形成的许多认识误区和思想混乱,而这些认识误区和思想混乱,又或多或少干扰、影响着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干扰、影响着文化传统的传承、发扬。
在如何看待文化发展、看待文化遗产保护继承的问题上,新旧对立、新旧截然分离的观点就是一种影响极大的错误认识。例如,由于简单运用“进化论”对待文化艺术,认定文化艺术的“发展”就是不断“进化”、不断“进步”,甚至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不破不立”,必须“推陈”才能“出新”,因而对待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主张“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强调“不破不立”,必须“先破后立”,只有“大破”才能“大立”。
这种思想长期指导支配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原应继承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民族传统及文化遗产(包括物质遗产及非物质遗产),全都被视为陈旧的、过时的、没有用处的,甚至是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是妨碍文化变革,妨碍“革命”事业发展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因此,对传统、对遗产从批判继承逐渐走向轻视和全面否定,最集中也是最极端的发展,就是所谓推倒一切旧文化的“文化大革命”。
为祸十年之久的“文革”,尽管其核心实际不是“文化”问题,但它确实是以“革”旧有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之“命”为旗号而发动的;而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更是一时响彻天际的运动口号,其大破坏之“千钧铁拳”,更是横扫了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其对人类文化(尤其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破坏,更是空前惨烈。它是传统文化及文化遗产的一场浩劫,必须完全否定这场所谓破坏民族传统“文化”的“大革命”。
本来,中国历来重视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约三千年前的西周“制礼作乐”,就是对当时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黄帝以来的“六乐”,如《诗经》歌曲及舞蹈)一次全面整理继承。历朝历代统治者,只要是雄才大略者,有见识者,只要是国势兴盛者,都非常重视以国家之力制定礼乐。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绵延不绝没有中断者,并且,中华文学艺术数千年漫长进程中一直精彩纷呈,高潮接踵出现,没有出现其他文明史上常见的中断和停滞,没有出现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那样的低谷,中国人民对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呵护、珍爱,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生了重要作用,其保护传承之功大焉。
当然,中国古代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者狭隘利益和儒家礼教教化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历来有“求新求变”、“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追求,加上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对文化遗产和传统保护经常形成冲击破坏。《易经》所讲之“易”,就是变易,重“易(变)”轻“常(经常、平常、常态)”,在文化方面也就是重创造轻积累,重“发展”轻遗产保护。司马迁著名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表述,以一“变”字高度凝练概括古今差异,揭示历史进程本质,固然精辟,但同时也是对文化传承积累的一种忽略。与今天文化保护的先进意识相比,与日本等国长期形成的传统继承观相比,我国古代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仍属于一种“自在”的、“自然”的状态,并没有达到自觉、自为的境界。
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的军舰大炮打破天朝迷梦,古老的中国突然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腐朽的清王朝一败再败,西方文化伴随经济、军事之强势长驱直入。中国社会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动荡变革时代。变革成了近现代中国的主要追求。“天演论”即进化论的引入,被广泛运用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激起社会上强烈的反思和变革的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旗帜,其功绩应该高度评价,但当时不少人主张“新文化”的同时,将各种传统文化、文化遗产与“旧文化”“孔家店”捆绑,主张统统打倒。不仅犯了“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的失误,还种下了新旧对立、水火不相容和“破旧立新”等对待文化遗产的激进倾向。例如胡适曾鼓吹“全盘西化”(尽管后来修正为“尽可能的全盘现代化”),鲁迅也曾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竟不读”中国旧书,也曾狠贬中医和京剧等传统遗产。这一时期对旧文化的否定,其实也是传统文化重“变”因子在特殊时空条件下的畸形发展。
百余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存续文化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发生严重改变。从清朝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八国联军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从新文化运动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文化发展遭遇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变革,文化传承所受周期性震荡的频率和激烈破坏的程度,为世界其他文化发展史所罕见。
痛定思痛,我们深感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不能简单运用“进化论”看待,也不能简单运用是新是旧或“先进”、“落后”等标准来裁决。本来,文化进化的思想,在欧洲历史上是生物学进化论和西方文化中心论相结合的产物。西方思想家和人文社科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在逐渐摆脱欧洲中心的偏见时,也有不少人主张文化价值相对论,以避免文化价值评判的简单化片面化。
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各有其历史、特点,其实并不像科学技术一样可以标准化和不断“进化”的。科学技术等文化成分的发展规律,是“推陈出新”、“后来居上”,文学艺术等文化成分却有自己的发展传承规律。文学艺术的发展历程,不是简单的“唯新论”即“新的就是好的”和“后来者必居其上”。因而,对待文学艺术作品及优秀的非物质遗产,绝不能机械地求新求变,不能简单地“喜新厌旧”。例如,后人雕塑的“维纳斯”,尽管成就斐然,但绝不可能因此否定、替代卢浮宫镇馆之宝古希腊的维纳斯。又如李白、杜甫的诗篇,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而明清以来多少新旧体诗作,在时间上(甚至内容上)新则新矣,也只有极少数或可比肩唐诗,但决不可能取李、杜而代之。同理,清代曹雪芹写出伟大小说《红楼梦》,其后新作车载斗量,恒河沙数,但在文学史上又有几部能与《红楼梦》相提并论?
科学技术不断更新,不断扬弃旧说,不断追求真理,科学强调统一标准,即“真理只有一个”。文学艺术不但可以、也需要“百花齐放”。因为文学艺术不仅表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特性,也体现了不同作者的鲜明个性,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拥有无限宽广的选择,追求种类、形势、风格“多多益善”,追求丰富多彩,并不会局限于“仅此一种(形式)”或“独此一家(作品)”。例如有了音乐不能就清除美术,有了戏曲也不能脱离开文学,喜爱舞蹈的人,也会喜爱雕塑。即就文学中的小说而言,有了长篇,不能清除短篇;我国有了最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红楼梦》,也不可能就此把原有旧的(原先便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优秀作品从中国文学宝库中清除,以《红楼梦》取代所有后者。今天的读者也不会因有曹雪芹而不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或要求把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赶出文坛、赶出书店。就连否定一切、大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只剩下“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不也是要有“八个”而非仅仅一个吗?“旧”小说《红楼梦》,不也因毛泽东青睐而独获生机,在“文革”中大量加印吗?
文化艺术需要创新,创新需要“推陈出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主张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有一定道理。但机械地执之为文化发展的总方针,教条地作为对待文化传统和遗产的总政策,则显然有误。原文所说之“推”本是“推开”、“推倒”、“排除”的意思,意味着“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之“破”,不是今天“推出新人”、“推进民主”、“推选代表”之“推”。以为必须先“推倒”旧的,必须先“大破”前人已有成果,才能“出新”,是把所有旧文化、旧传统、文化遗产,与创新截然对立。果如此,第二句“推陈出新”就是对第一句“百花齐放”的否定或限制,因为陈花旧花就必须清除推倒,不得再行开放,所谓“百花”,便只剩“新花”,即唯有新花才能生存展示。殊不知今日之新花,明天必成旧花,甚至不待明日,转眼就已变旧,于是“百花齐放”也就无法实现。实践证明,文革式的“推陈出新”,正是对文艺百花园的残酷摧残。唯有一片凋零,哪来春色如许?
其实如前所述,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新、旧,并不对立。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所指出,人们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必须在前人创造的“思想材料”的前提下进行。列宁也反复说明无产阶级的文艺,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学习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统一关系,不仅不矛盾,反而是文化艺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是新人成长的必由之路。正如齐白石所说“似我者死,学我者生”,关键看你如何学习如何继承传统。从辩证的观点看,没有旧,何来新?旧之不存,新何以见?昔日之旧,不也从新中来?今日之新,不就是明日之旧?其实,学习继承传统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创新过程,因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领会,有自己独特的识见。“文革”中大力宣传毛泽东读《红楼梦》,竟然发现了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这个例子生动说明,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学习和再认识,也是创新过程,“学”字当头,“创”也就在其中。中外艺术史表明,凡是有大成就的创新的艺术家,无不认真学习、继承前人优秀传统,尤以开宗立派的大师为最。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和郑板桥、齐白石甘当明朝大写意画家徐渭(徐青藤)的“门下走狗”,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今天,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举国奋斗的目标。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与现代化进程有无矛盾?值得思考。这也是“新、旧”问题在新形势下的体现。机械地以“时代进步”以“现代化”为尺度,以科学技术的“先进”“落后”断是非,就会荒唐地得出这种结论:《楚辞》比《诗经》,更“先进”更“现代化”;《唐诗》比汉魏乐府、比《诗经》、《楚辞》更“先进”更“现代化”。于是,“最现代化”也就是“最先进”的,只有发达国家的现代派艺术或后现代派艺术了!只有西方的最新流行文艺了!其实,文学艺术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也有自己的优秀准绳,就是好与坏,美不美等等。我们将依据文学艺术及文化遗产自身的评判标准,来学习继承优秀文学艺术传统,实施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另一个被忽视的地方,是以为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的继承轻而易举。其实,正如梅兰芳所说,传统是前人给我们的宝贵馈赠,我们这一代人要努力提升自己,才能使自己配得上这份礼馈赠。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甚至要经历艰苦奋斗,使自己达到能够俯视人类文明的高度,才能真正认识民族传统之精华,认识文化传统何以为优,何以为劣,才能从中最有效地吸取其养分,也才能更好地传承文化,保护遗产。
走出新、旧对立的认识误区,既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思想前提,也对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彻底清除“文革”左的思维遗毒有重要推动。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随着“文化自觉”的实现,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将迎来新的百花齐放的可喜新局面。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秦 序